
最近,一个叫“二舅”的老人和他的故事火了。
二舅和他清贫中闪闪发光的人生,看哭了全网人。被称为2022精神内耗最佳治愈。
小视却想到了这么一个沉默而小众的故事——
建立在西藏无人区的保护站,常年驻守着三个巡护员。
这里人迹罕至,巡护员的生活重复而单调。
直到有一天,一个不速之客的闯入,打破了这片平静。
那是一头虚弱的小野牦牛。


小牛在它出生第二天,不小心从野牦牛队伍中落了单。
它还没断奶,根本没有独自觅食的能力。
失去了妈妈的保护,小牛奄奄一息,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三个巡护员决定收养它。
于是,小牛成为这里的第四个成员。


没想到,跟人类生活在一起的小牛,逐渐哈士奇化。
每天早上,它会跟着巡护员一起列队跑操。
跟着“一二一”的口令,小牛连节奏都卡得准准的。
巡护员端上早餐奶的时候,它又是蹭头又是摇尾巴。
这小牛,怎么还有点狗里狗气呢。



小牛跟巡护员的关系亲密无间。
有人好心告诫巡护员,养野牦牛可要小心啊。
它长大了说不定会用角顶人,劲儿稍微一大,人的身体可遭不住。
但巡护员觉得不可能,从小养的牛,它早已成为家人。
壮硕的小牛常常依偎在巡护员身边,还喜欢用舌头舔他。
巡护员不乏炫耀地抱怨道:“小的时候舌头还是软软的,现在大了,舔的时候都有点喇脸。”



小牛长到六个月的时候,隆冬来袭。
它平常喝的牛奶没了供应,眼看着就要遭遇断奶危机。
巡护员凑钱买来一箱一箱的牛奶,可是全部倒在一起,不需两顿,小牛就咣咣喝完了。
巡护员只能上山帮牧民打水、捡牛粪,用劳动力换来鲜奶。
小牛“牛生”的第一个冬天,在所有人的百般努力之下,终于安然度过。


原本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。
直到一个身影,出现在保护站的附近。
一只成年野牦牛。
那可能是野牦牛群的首领,也可能是小牛的妈妈。
它时不时出现,站得远远的望着他们,仿佛在无声地呼唤小牛回家。


第二年夏天,巡护员把小牛放了生。
它长得健康又强壮,再也不是最初那个羸弱的小生命。
所以,也是时候回家了。
回归那片荒野,那片隐藏着自然力量的众神之地。


这个小故事,出自纪录片《众神之地》。
这是一部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文自然纪录片。
创作团队跨越了中国四角,探寻了四种令人敬畏的动物——
雪山使者野牦牛、海上精灵白海豚、雨林巨无霸亚洲象、森林之王东北虎。
它们都是食物链顶端的动物,代表着那一方自然生灵。
面对它们,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动物的关系。
我们该如何看待它们?它们又在怎样看待我们?


这部纪录片中的所有动物,都仿佛拥有自己的品格。
比如野牦牛篇中,小牛只是插曲,真正的主角,是两头雄野牦牛。
一个叫昆仑。


昆仑成长在山脊之上。
荒野的肃杀和辽阔,赐予它桀骜不驯的灵魂。
只是站在人的审美角度,都能感受到昆仑的帅气逼人。
黢黑茂密的毛发、黝黑深邃的瞳孔,仿佛山神附体般,不怒自威。
昆仑无疑是躁动的、危险的、令人不安的。
它的每一次出现,都让牧民捏一把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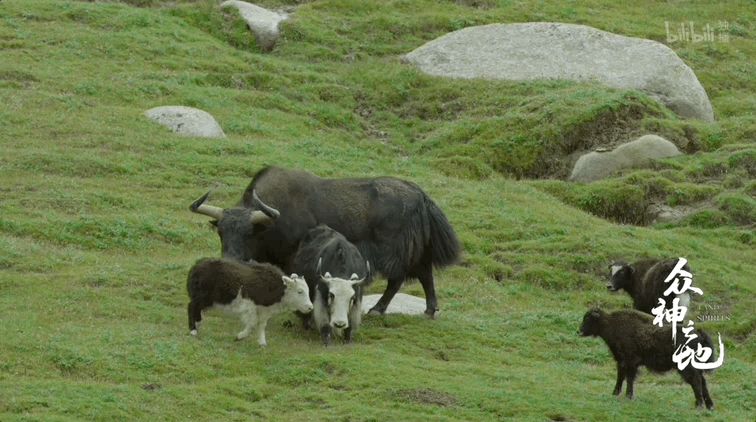
每年夏天,是野牦牛交配的季节。
昆仑会不请自来,从雪山一路走到草原,闯入牧民放养家牦牛的区域。
凭借着比家牦牛大一圈的体格,昆仑很快就成为这片牦牛群的新主人,肆意寻欢作乐。
这下牧民就犯了难。
昆仑一来,它天然的野性气质总能唤醒家牦牛被压抑的本能,变得躁动不安。
别说管理,连去给它们采奶都费劲。


所以牧民们对昆仑是又怕又烦。
这个混世牛魔王般的存在,谁的牛群遇上谁倒霉。
但谁又能说,牧民之于昆仑不是入侵者呢?
他们甚至不是同样的物种,却统治着牛群。
昆仑和牧民之间,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博弈。
一场关于自己领土和子民的争斗,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。


昆仑的反面,则是断角。
断角,字如其牛,一只角是断掉的。
这是年轻气盛时打架的后果,是属于断角的功勋章。
不过,如今的断角,垂垂老矣,早已没了戾气。
和昆仑相比,断角更温和,仿佛一个秉持着中庸之道的老头儿。


它无心和牧民作对、争夺子民和领土,只想躺平。
在牛群中颐养天年,是断角最大的诉求。
狡猾的断角选择“入赘”到牧民家,自愿成为种牛。
毕竟,野牦牛的基因,可是牛群提升体质、抵御严寒的关键。
断角为家牦牛提供优质基因,牧民为断角提供养老活动中心。
他们成了奇妙的利益共同体。


昆仑和断角作为野牦牛的两种类型,都以自己的方式跟人类互动。
亦张亦驰,甚至是共生着。
同样的关系,还发生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带的渔民和白海豚之间。
渔民捕鱼的淡水区,如果生态环境足够好,说不定会看到白海豚的身影。
都是为了捕鱼,渔民和白海豚有着无声的默契。
有白海豚的地方就有鱼;
渔民下渔网的地方就有鱼。
他们宛如一起工作的伙伴,在海上形影相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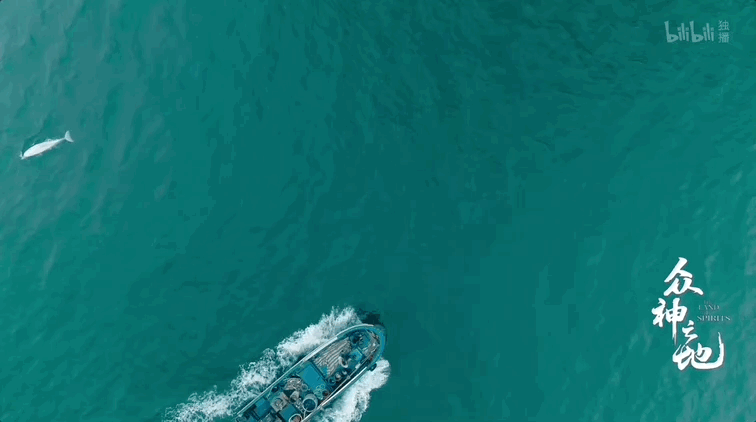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些高度依赖大自然的地方,我们看到了人与动物原有的相处模式。
他们深深地连结着,作为大自然的两方生命体。
能量和地位自由流动,没有谁统治着谁,没有谁主宰着谁。

《众神之地》想要讲述的,就是这样的故事。
导演的手记中解释了片名的含义:
「什么是众神之地?」
“简单说,众神,是几种动物,曾经是图腾,是神的化身。
这些动物,是大自然的晴雨表,是自然意志的展现,正如萨满会通过虎神与天地沟通。
往大了说,万物也许都算众神。所以众神之地,其实就是自然。”


在我们祖先生活的年代,跟自然直接沟通,是人类必备的技能。
“类似于第六感,就如同旧时的农人能预知天气,猎人能嗅出动物的远近,那是生存的本能。”
动物之于人类,是预兆、是福音、是神谕。


世界各地的神话故事中,都有动物的身影。
在语言还未诞生的时候,壁画上就有了牛。
在藏族传说中,牦牛,是山神的家畜。
“当世界第一缕阳光照耀到冈仁波齐时,便有了第一头牦牛。”


传说中,野牦牛是奉山神的命令,帮助人类在荒野立足的。
它们帮人类驮重物,贡献出毛御寒,贡献出奶充饥。
藏族人民这才得以在这里生存下去。
《斯巴宰牛歌》中唱出了对牦牛的敬意——
牦牛的头颅变成了高山;
牦牛的皮张变成了大地;
牦牛的尾巴变成了江河。
西藏每年举办祭祀典礼,僧人要戴上28种绘制而成的动物面具,跳舞祈福。
第一个面具,就是野牦牛。


纪录片中,一个僧人为了制作面具,专程到荒野上捕捉野牦牛的身影。
在此之前,僧人从未见过野牦牛。
僧人在荒野上寻觅,但真正看到它的瞬间,反倒平静了下来。
僧人和野牦牛远远对望着,如同祖先们千百次做的那般。
感受着它的气息,仿佛来自远古的神灵。


而关于白海豚的神话,最出名的,当属妈祖的化身。
每年农历三月,渔民祭拜妈祖的时候,正是白海豚开始活跃的时候。
因此,白海豚,还被称为“妈祖鱼”。
除了妈祖神话,还有一个传说——
清代,白海豚在珠江口一带,被称为卢亭。
卢亭是传说中一种半人半鱼的生物。
南宋时期遭到围剿,卢亭的生活范围不得不从陆地退入海中。


这跟白海豚的习性也隐约对照着。
白海豚作为大型海洋生物,却通常生活在距离陆地不远的淡水区。
刚出生的时候,通体呈深灰色,随着逐渐长大,灰色褪去,变成通体雪白。
等到白海豚老去,它又会泛起粉色。
当它通体粉红、行将就木的时候,总是对陆地有着莫名的渴望。


纪录片中,刻画了一个老年白海豚的最后时刻。
在广东省台山市,一只老年白海豚从烽火角入海口缘河而上,误入内河三十多公里。
据推测,这只白海豚的年龄大概30岁,相当于人类的70岁。
它的声纳系统,已经不足以支撑辨别方位。
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它找不到方向,身上长了霉菌。
为了帮助它回归大海,人们开船用声音驱赶。


然而,就在人们把这只老年白海豚送回大海的4天后,它的尸体被发现了。
它死在了距离入海口不足3公里的河中。
海豚救助员说,自己参与过的白海豚救助活动,从来没有成功过。
一切都宛如神话故事的结局。
从陆地到海洋的卢亭,无论如何都要在晚年回到陆地。
即使这片陆地早已不属于自己。


这些生灵,曾是文明的图腾,是人类与大自然沟通的桥梁。
这些神话,曾是百姓们口口相传的、对自然古朴的敬畏。
它们是这片土地最精妙的设计,是古老的神迹。
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们忘记了这份敬畏,甚至想把它们为我们所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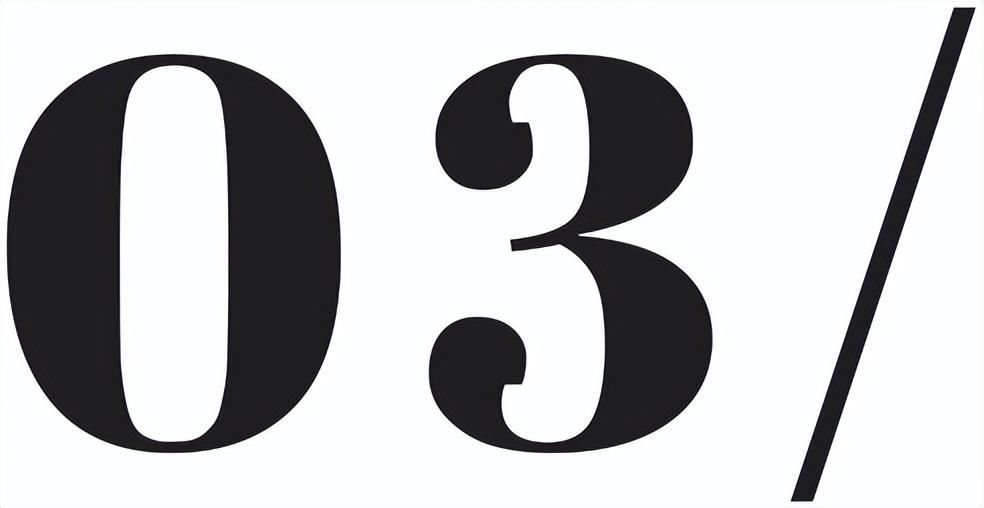
人类对自然的改造,往往以人类的生活发展为出发点。
比如沿海地区常见的生产作业形式,抽沙。
巨大的机器轰隆隆作响,与此同时,这片水域的一整条食物链因此断裂。
白海豚作为食物链顶端,受到很大的冲击。
为了寻找食物,白海豚冲撞进渔网密布的养殖区,也是常有的事。


中华白海豚江门保护区的标本馆里,有着各种各样白海豚的死态。
这些死态,如同人类的“罪证”。
死去的白海豚,有的身上有螺旋桨划伤的痕迹,有的尾部被渔网勒住。
最让人感到惊悚的,是一条没有尾巴的白海豚尸体。
尾巴的切口整整齐齐,应该是螺旋桨打断的。
标本馆的工作人员应渔民报告,把这个尸体带回了馆里。
打开它腹腔的那一刻,所有人都呆住了。
这个尸体里,还有一个完整的海豚婴儿的尸体。


它还保持着在妈妈肚子里的状态,眼睛也闭着,就好像睡着了一样。
如果妈妈没有被螺旋桨杀死,那三四个月后,它就可以从妈妈肚子里出来了。
何其残忍的一幕,在无声地向我们控诉着。
自私的人类,都做了些什么啊......
然而,这样的画面我们看得还少吗?
全球变暖,瘦骨嶙峋的北极熊不得不啃食人类留下的垃圾;
酷暑难耐,动物园里的北极熊热到奄奄一息,甚至全身皮毛都变了色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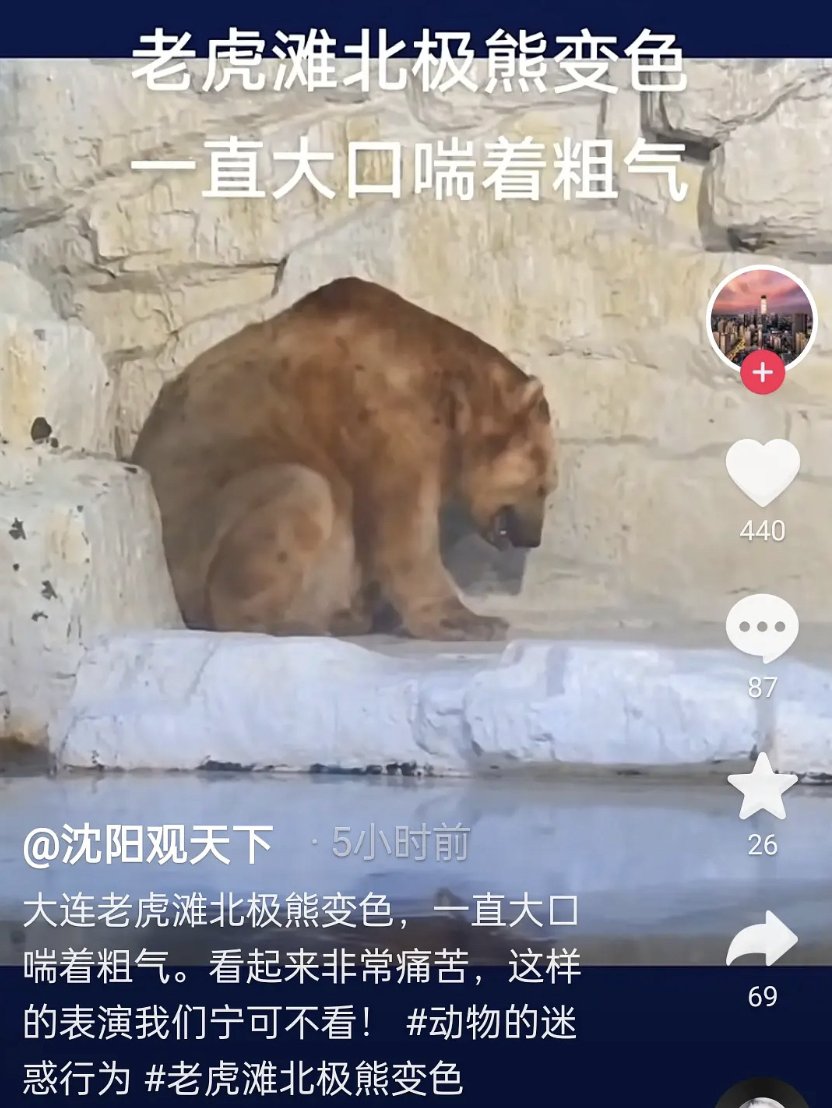
图源:《小小的追球》@沈阳观天下
去年,浩浩荡荡的云南象群迁徙,成为奇观。
然而奇观的背后,是亚洲象退无可退的生存处境。
“自然界中,没有一个物种是想毅然决然地离开故土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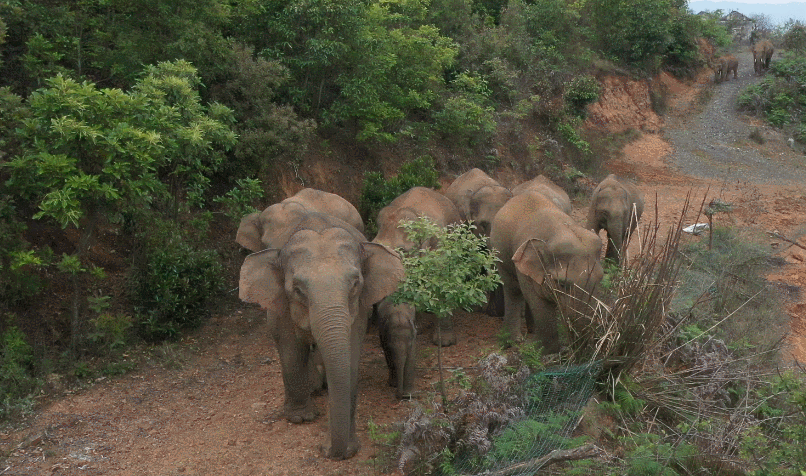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自封为地球的主人,万物的主宰。
为了证明人类的「伟大」,我们还把动物们关进牢笼。
圈养它们,驯化它们,把它们变成玩具,供人类观赏和戏弄。
它们确实是聪明绝顶的,远超动物原有的能力。
大象学会了拿大顶;
海豚学会了顶球;
海豹学会了算数;
狗熊学会了钻火圈;
猴子学会了骑单车。


可是曾几何时,它们不是任人宰割和观赏的畜生。
是什么,让我们忘记了应有的谦卑。
忘记了这是一片众神之地,而非人类的游乐园。
每次聊起动物保护的话题,总有人说,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,不要圣母心泛滥了。
但最近的一条新闻告诉我,这些老生常谈的内容,我们不仅要说,还要反复地说。
2022年7月21日,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发布全球濒危物种红色目录更新报告。
正式宣布长江白鲟灭绝。


长江白鲟是中生代白垩纪残存下来的极少数远古鱼类之一,在这颗星球上存在了一亿五千万年。
它是和恐龙同时代的生物,然而却消失在了人类时代的今天。
长江白鲟的灭绝,或许只是一场物种大灭绝的先兆。
早在上个世纪,就有大约200万个物种相继灭绝。
如今,全球变暖,海水酸化,生态仍旧在进一步恶化。
没有人知道,还有多少物种正在消失的路上。
我们理应反思,我们理应警醒。
“每一个经过自然之手点化的物种,都是存留于世的神迹。”
这里曾是一片众神之地。
每一个生灵,都在这里生存、繁衍、缔造神话。
如今,众神纷纷选择离我们而去。
那我们面对的,将会是什么呢?




